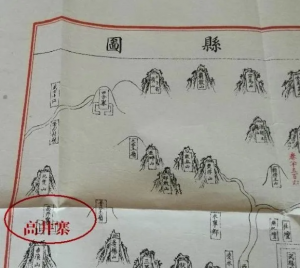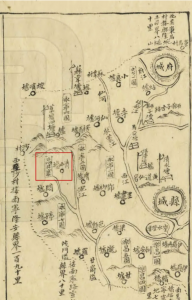这里的三月份总是让人非常恼火,这时正好是回南天最严重的季节,宿舍内外堆满潮湿的衣服,空气中散发着发霉的味道。每年回南天的季节,从海边吹来的暖湿空气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,在岭南地区形成准静止风,使得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、非常潮湿,期间有小雨或大雾,冰冷的物体表面遇到暖湿气流后,就开始在物体表面凝结、起水水珠。宿舍的窗户和水泥地板上结满水珠,甚至连刷过油漆的木箱表面也变得潮湿。
阿克摸一下自己那几件没有晒干的衣服抱怨:“如果再不出太阳,我都要长霉了。”
“天气预报说未来一周都是回南天,你估计可以实现长霉的愿望。”我刚刚去阿新家里拿东西的时候,电视正播放天气预报。
这时候阿宝给建议:“我从报纸上看到,说如果在宿舍点一盆炭火可以驱除潮气,不过学校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干。”
阿丹不支持这个做法:“我们连烧炭的钱都没有,木炭只有过年打边炉的时候才能用,可贵着呢。”
我听完之后告诫:“封闭空间烧木炭,小心一氧化碳中毒,化学课可是专门警告过。”
阿克感到绝望:“难道真的还要忍受半个月吗?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?太阳公公,请求你早点出来吧。”
确实没有什么办法,只能一直等到回南天过后,干燥的空气才会把这些湿气带走。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,衣服不干透也穿在身上,利用体温把它烘干。我听说十七班有学生带一周的衣服,每周带回去用洗衣机洗,两天就可以晒干。上周返校前,我爸爸说要这周要购置一台洗衣机,我非常期待,希望它能够让我彻底摆脱回南天的困扰,虽然我不会像那位同学一样积攒一周的衣服,但是至少可以用来洗那些厚重的衣物,特别是被单和被套。
终于等到周日,现在毕业班周六也上课,每周自习到周日上午,下课之后可以回家带米和准备各种生活用品。我满怀期待地回到家,却没有看到洗衣机,而且家里一个人都没有,问邻居,原来家人都去大伯父家,全族人正在给太奶奶过九十大寿。
我出门向大伯父家走去,大老远就看见他家门前挤满人群。我进门看见太奶奶坐在大桌子的边上,头上戴着深色的毛线帽,虽然已经九十,但是她精神很好,只是牙齿都已掉光,她抱着重重孙女,我才想起来大伯父的大儿子上个月生的女儿今天也正好满月。我看见一群人围着太奶奶说笑,她也是笑眯眯地听着,太奶奶自己肯定也想不到,她和太爷爷的后代现在加起来已经将近一百人,老舍先生写过四世同堂,如果他出生在我这个家族,不知道他的小说会不会改名成:五世同堂。
我去厨房和爸爸打招呼,作为村里有名的村厨,这个时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爸爸正在做鲶鱼焖豆腐,这是他的拿手好菜,今天这道菜也是专门为太奶奶而做,太奶奶非常喜欢吃这道菜,她小时候经常能吃到家人做的鲶鱼焖豆腐,她跟我们说过她的祖先和这道菜有着非常深的渊源。
太奶奶姓朱,朱家一直住在圩头的公路旁边,很久以前朱家是贫苦人家,有一天家人从田间捉回一条野生鲶鱼,一条鱼根本不够一家人吃,就用豆腐和鲶鱼一起焖煮,没想到这样一来,不仅鲶鱼好吃,渗入鱼汁的豆腐也美味无穷,于是这道菜成为朱家赞不绝口佳肴,后来当地村民纷纷效仿制作,鲶鱼焖豆腐逐渐成了这里人宴请宾客的必选菜。
我爸爸说这道菜讲究原汁原味,必须用柴火灶烧制才能煮出本来的味道。我看见他正在切一条处理好的野生河鲶鱼,旁边的碗里装的是与鲶鱼等量的土制水豆腐,水豆腐已经用油煎成金黄色,旁边还有备好的西红柿、鲜葱杆、花生油、八角粉、黄酒等各种配料。他切完之后,先用花生油把鲶鱼块也煎成外表金黄,然后把煎好的水豆腐和鲶鱼块一起倒入锅中,加入配料并盖上锅盖用柴火灶焖炒,过了五分钟后,加入鲜葱杆拌匀,最后盛到一个大碗中。
旁边的三叔公看见我后说:“阿靖,把这盘菜端上去给你阿太尝一尝。”
“好的。”我接过盘,小心翼翼地端到太奶奶坐的桌子。
太奶奶用筷子尝一块豆腐和一点鲶鱼,我看见她一边嚼一边看着这碗鲶鱼豆腐,我想她一定想起自己的父亲,想起小时候吃这个味道的感受,更想起自己这九十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。
我鼓起勇气,当着叔叔婶婶们的面祝贺太奶奶:“太奶奶生日快乐,身体健康,万寿无疆!”
她没有回答,三叔公凑到她的耳朵大声的说:“阿靖给你拜寿了,就是阿广的儿子。”
“我记得阿靖,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她抬头看着我,连着点好几次头,我相信太奶奶一定还记得我,她和阿展叔他们一家住在一起,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。
这时候三叔公转过来对我伸个大拇指:“今年中考一定要考中,太奶奶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过了不久,阿霍过来叫我去吃饭:“你终于回来了,我昨天就请假回来,一起吃午饭去吧,我们上初中的后生坐在一桌吃饭。”
我坐下的时候,发现大伯父也来我们这一桌,刚刚当上爷爷的他显得异常高兴:“你们这桌是有机会考上大学的人,你看太爷爷这一支已经快一百人了,都没出过一个读书人、更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,你们要加油。”
我听完心想着下一句肯定要拿我来说事,我果然没猜错。
“现在这里最有希望就是阿靖。再过两个多月就中考吧?一定要考上武缘高中,给太奶奶、给我们家族争光。”他说得兴奋起来。
虽然我一直很骄傲,但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,我还是很害羞,我红着脸回他:“要考完才知道,而且不只是我,这里的人都有希望。”
“有些人肯定是没希望了,比如阿霍就不行,他会考结束之后就得回来干活,然后去广东打工。”
他毫不留情面地这么说自己的儿子,阿霍没有反驳,也没有尴尬,想必他已经习惯,甚至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计划。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的爸爸一直也这么说我,或许我也不会想着努力学习。
我不喜欢大伯父这么说话,却很乐意听他讲自己参加越战的经历,大伯父当时是以民兵的身份参加中越战争,镇上总共派出十二个民兵,在这之前他们都没有上过战场,甚至有些人连枪都没有摸过,很幸运的是,这十二个人都活着回来,这一段佳话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大伯父经常会跟我们讲诉这个传奇,喝了几杯酒之后,今天他又开口讲诉这段让他引以为豪的经历:
“那时候我们十二个人来到前线,到处都是轰隆隆的炮弹声音,所有人都很害怕,生怕炮弹打到自己,炮弹打得近的时候有人还尿裤子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用枪,大家基本都只是听指挥,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民兵都是按镇编排班,灵镇的十二个人编在同一个班,我们到的那时候战斗很激烈,前线已经死了很多人,那些刚刚换下来的人说每一批上去的人都死掉大半人。我们是倒数第二个班,正准备要派我们上前线的时候,指挥官发现人没有到齐,派人去找,原来有两个人睡着了,怎么叫都叫不醒,眼看着到时间,指挥官让倒数最后一个班上去顶,后来这个班的人全都被炸死。正要派我们上去的时候,总指挥说牺牲太大,暂时停止进攻。
“不久之后增援的部队赶到,灵镇的这批民兵就全部安排在后面扛大炮和扛担架,不用再到前线,镇里去的十二个人全活回来。你们这是为什么吗?这是灵镇的山神显灵。那两匹神马在关键的时候,托梦让那两个人沉睡不醒,挽救了我们十二个人的性命,不然当时顶上去也是白白送死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是神马显灵呢?可能他们就是太累醒不过来。”有人质疑这个山神显灵的说法。
“你们不知道,在那种地方,别说沉睡,闭一下眼睛你都得留个神,说不准什么时候炸弹就过来。他们两个人睡成那样,怎么都叫不起来,不是山神显灵还有什么?”
又有人问他:“真正的大炮长什么样子?声音大吗?”
“大炮跟在电视上长得差不多,不过声音没那么清脆响亮,倒是和清明节放的大炮有点像。”
“越南长什么样呢?听说你当时进入越南境内?”我非常好奇。
“越南和我们这里也差不多,那里山也很多,他们也很穷,甚至比我们还穷呢。我们跟着部队一直打到靠近越南的境内地区,后来我们开始撤退,撤退的过程中埋下了很多地雷,他们在我们撤退之后也埋下很多地雷。”
我经常看到新闻提到边境的排雷英雄,听他说得正高兴,我又问道:“你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过那些地雷吗?”
“没看到,我们是从其他路撤回来,埋雷的地方都是在山里,那些地雷很可怕,你要是踩到了就没法活命。”
我一直听说越南离我们很近,所以很想去看一眼那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,不过我现在最远也就是到过县城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去一趟。
吃过晚饭,我就返回学校,刚进教室不久,隔壁班的阿军给我送来一个奖状,这是上次化学竞赛的奖状,我和他只拿到县级三等奖。
他递给我的时候感叹:“老师觉得非常奇怪,一中那几个人都是拿一等奖或者二等奖,我们两个表现太差劲。”
我安慰他:“我听说那天他们包一辆小车去,不会像我们坐车晕成那样,我们能拿到奖就很不错了。”
“我觉得和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,听老师说县城的学生有两个拿到省二等奖,差一点就拿到一等奖。”
化学老师说过拿到一等奖的学生就可以入选国家集训队。
这时候我又想起那位叫田茉的女生,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两个学生中的一个,想到她我的内心不禁觉得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,一股奋发努力的劲头涌上来,这个似乎和理想一样能激起我努力的动力。
我对着奖状呆呆想了几分钟,直到铃声把我叫回现实,想起来还有一场重要的考试在前方,于是拿出课本,随着同学们的朗读声开始大声地晚读,努力背诵诗词古文。